译文及注释
创作背景
冯延巳 (903--960)又名延嗣,字正中,五代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在南唐做过宰相,生活过得很优裕、舒适。他的词多写闲情逸致辞,文人的气息很浓,对北宋初期的词人有比较大的影响。宋初《钓矶立谈》评其“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其词集名《阳春集》。
猜您喜欢
泥金小简,白玉连环,牵情惹恨两三番。好光阴等闲,景阑珊绣帘风软杨花
散。泪阑干绿窗雨洒梨花绽,锦澜斑香闺春老杏花残,奈薄情未还。 走苏卿
聪明的志高,懵懂的愚浊。一船茶单换了个女妖娆,像章城佛了。老卜儿接
了鸦青钞,俊苏卿受了金花诰,俏双生披了绿罗袍,村冯魁老曹。
 冯延巳
冯延巳 白居易
白居易 孙樵
孙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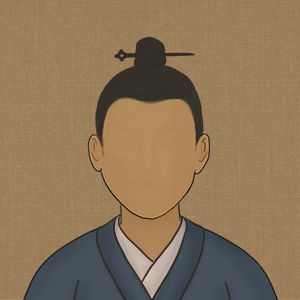 刘庭信
刘庭信 白朴
白朴 王国维
王国维 刘基
刘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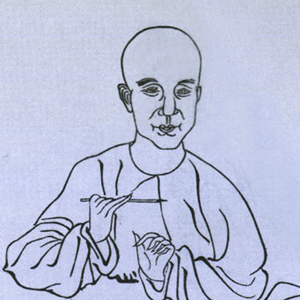 项鸿祚
项鸿祚 吴伟业
吴伟业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