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游
木翳兮林深,境幽兮径平。峰高兮月小,涧古兮泉清。
雾氤氲兮图形,水飕飗兮琴声。春欲暮兮乌啼花落。
秋将至兮鹤唳猿鸣。膏吾车兮整吾驾,将有事兮林坰。
爰发爰启,载兴载征。访仙人兮琳宫扣释子之玄扃。
高揖浮邱远邀广成。拾丹田之瑶草,采翠巘之琼英。
掘栖烟之枸杞,斸含露之猪苓。驻予颜兮长春,延予年兮遐龄。
与日月兮同光,偕天地兮不倾。蔽明兮掩聪,凝神兮啬精。
心清兮欲寡,体安兮气宁。绝交息游罢送休迎。不记晦朔,宁知亏盈。
不事王侯,宁识公卿。虽乏钟鼎之贵,终无鈇钺之刑。
尘缰莫系,世网曷萦。得失一致,宠辱不惊。何必论泰山之重鸿毛之轻。
麻衣之贱金章之荣。又何必计蝇头微利蜗角虚名。
长途扰扰,闹市营营。蹈草庐之高躅,诵陋室之佳铭。
土床石枕雾帐云屏。依稀和靖彷佛渊明。玩庭梅之冷艳,嗅篱菊之秋馨。
听莺鹂之求友,呼鸥鹭以完盟。展奇松之轩盖,铺软草之毡茵。
临清流兮洗耳,汲沧浪兮濯缨。躬耕幽屿,独钓荒汀。
酒船茶灶,诗卷棋枰。樵渔宾客,牧圉弟兄。更唱迭和,极论深评。
云边横笛,月下吹笙。随心去住,任性纵横。缅思畴昔,庆快平生。
襟怀洒落,胸次峥嵘。逍遥丘壑,放浪身形。悠然遗世,脱尔忘情。
回视彼抗尘走俗之辈,蜂房课蜜之功甚时可办,蚁穴封侯之梦何日能醒。
亦何异于填海之精卫,良可悲夫烧空之火萤。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耐惊耐怕黄虀瓮,长满长干老酒盆,一贫尽可张吾军。休忘本,樽有酒且论文。
胸中太华身难憾,舌底狂澜口且缄,看渠暮四与朝三。呆大胆,樽有酒且醺酣。
周郎赤壁鏖兵后,苏子扁舟载月秋,千年慷慨一时酬。今在否?樽有酒且绸缪。
芸窗月影吟情荡,纸帐梅花醉梦香,觉来身世两相忘。休妄想,樽有酒且疏狂。
岁云暮矣虽无补,时复中之尽有余,老来吾亦爱吾庐。清债苦,樽有酒且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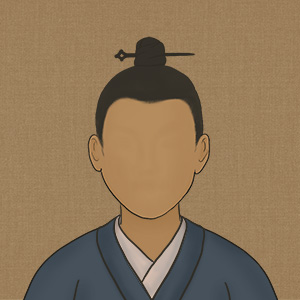 叶颙
叶颙 司马迁
司马迁 薛昂夫
薛昂夫 卢挚
卢挚 张可久
张可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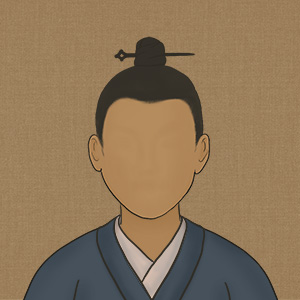 徐再思
徐再思 牛希济
牛希济 韦庄
韦庄 施耐庵
施耐庵 温庭筠
温庭筠 陈允平
陈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