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屋啼怪鸮行为郑文学超记其烈妇刘氏事
暗屋啼怪鸮,荒门逸瘈狗。鬼兵渡浃来,海城已无守。
昼天黄温温,凋阳不成曛。似有五色虹,宛委城西闉。
西闉茅盖楣,烈妇之所栖。烈妇留金氏,嫁为郑生妻。
烈妇有两女,烈妇有两儿。大儿十许龄,少女襁褓持。
少儿同大女,娇笑痴能啼。郑生苦佣书,烈妇苦织丝。
佣书复织丝,寒絮饥则糜。烈妇不怨贫,郑生不怨贱。
圭珏埋暗沙,精采有谁见?辛年八月杪,鳌柱东南倾。
河水无寸止,路泥无尺平。河水多流尸,尸流水不洁。
腥风扬路泥,路泥有人血。生曰吾死忠,妇曰妾死节。
死节妾匪难,奈儿若女何?大树遭斧斨,安顾墙隅花?
死忠生匪难,奈何以为家?倾筐不可理,摛手愁乱麻。
烈妇语生前,点首泪洏涟。妇还语大儿,外家城南偏。
速往匿外家,鬼将踰邻墙。而娘有而爷,而爷男子强。
顾娘及弟妹,兼难顾儿生。鬼去儿再来,再来看而娘。
狒狒掉长尾,抢入西家庐。西家有妇姑,赤裸遭毒痡。
仰掌不及梁,俯首不得池。求死不能死,噤口哑哑呼。
亦有好男子,喁喁同槽猪。生云祸将及,妇云咄已急。
将鸩置酒中,缶斝流殷红。殷红琉璃光,大女汝来尝。
饮女递饮子,女殒子同死。怀中顾幼女,三年未离乳。
母死谁乳儿,此酒儿饮之。少女饮不辞,死得娘慰怡。
维时万类盲,髡钳堕元槁。斗室万古天,日月两心皎。
对卺何从容,正袂敢草草。魑魅窥其庭,反奔戒滋扰。
郑生有弱弟,入门见死嫂。可怜死嫂怀,犹将死女抱。
死嫂死在床,死兄死在地。死嫂身已寒,死兄死馀气。
有气殆可活,救之获渐苏。救之虽得苏,活我诚何辜?
忍以同命鸟,使其泉下孤。屋漏相神明,坦誓难模糊。
莫云郑生生,郑生心已死。死心从死妻,生身怙生子。
莫云烈妇死,烈妇魂实生。夜夜房屋隅,静闻呼儿声。
郑生吾旧友,负才称不羁。贻书告我详,属我哀以诗。
烈妇身中材,烈妇端容仪。夙见井臼间,枲布整裙鞋。
昔为草霜洁,今为河星稀。河星照独桑,独桑无蜷枝。
独桑如女贞,百尺青青枝。下有病马嘶,上有哀雏啼。
姚燮(1805—1864)晚清文学家、画家。字梅伯,号复庄,又号大梅山民、上湖生、某伯、大某山民、复翁、复道人、野桥、东海生等,浙江镇海(今宁波北仑)人。道光举人,以著作教授终身。治学广涉经史、地理、释道、戏曲、小说。工诗画,尤善人物、梅花。著有《今乐考证》、《大梅山馆集》、《疏影楼词》。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香添索笑梅花韵,娇殢传杯竹叶春,歌珠圆转翠眉颦。山隐隐,留下九皋云。
陵阳客舍偶书
梅擎残雪芳心耐,柳倚东风望眼开,温柔樽俎小楼台。红袖客,低唱喜春来。
携将玉友寻花寨,看褪梅妆等杏腮,休随刘阮访天台。休洞窄,别处喜春来。
和则明韵
骚坛坐遍诗魔退,步障行看肉阵迷,海棠开后燕飞回。□暂息,爱月夜眠迟。
春云巧似山翁帽,古柳横为独木桥,风微尘软落红飘。沙岸好,草色上罗袍。
春来南国花如绣,雨过西湖水似油,小瀛州外小红楼。人病酒,料自下帘钩。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莫惜金尊倒。凤诏看看到。留不住,江东小。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百岁,从今尽是中书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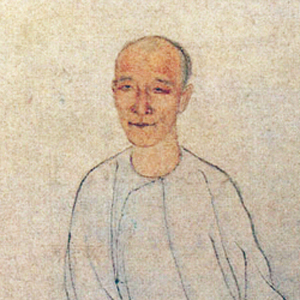 姚燮
姚燮 司马迁
司马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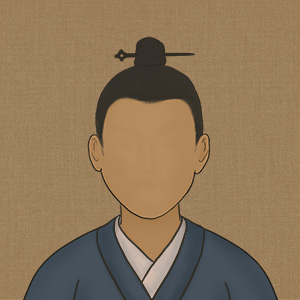 舒頔
舒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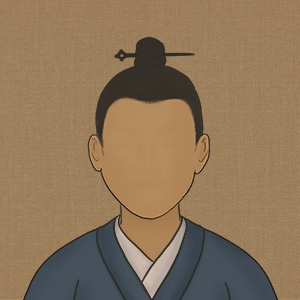 周文质
周文质 卢挚
卢挚 张先
张先 蔡挺
蔡挺 屈大均
屈大均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辛弃疾
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