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鉴赏
施绍莘(1581~约1640) 明代词人、散曲家,字子野,号峰泖浪仙,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有俊才,怀大志,因屡试不第,于是放浪声色。建园林,置丝竹,每当春秋佳日,与名士隐流遨游于九峰、三泖、西湖、太湖间。他兴趣广泛,除经术、古今文外,还旁通星纬舆地、二氏九流之书。善音律,一生所作以散曲及词著名,有《花影集》传世。另外,其词作多哀苦之音,既寄寓着作者命运多蹇的身世悲凉,又是明王朝灭亡前夕人们情绪的反映。如□谒金门□"春欲去"写有"无计可留春住,只有断肠诗句。
猜您喜欢
一水奔流叠嶂开,溪头千步响如雷。
扁舟费尽篙师力,咫尺平澜上不来。
山上风吹笙鹤声,山前人望翠云屏。
蓬莱枉觅瑶池路,不道人间有幔亭。
玉女峰前一棹歌,烟鬟雾髻动清波。
游人去后枫林夜,月满空山可奈何。
见说仙人此避秦,爱随流水一溪云。
花开花落无寻处,仿佛吹箫月夜闻。
千丈搀天翠壁高,定谁狡狯插遗樵。
神仙万里乘风去,更度槎丫个样桥。
山头有路接无尘,欲觅王孙试问津。
瞥向苍崖高处见,三三两两看游人。
巨石亭亭缺啮多,悬知千古也消磨。
人间正觅擎天柱,无奈风吹雨打何。
自有山来几许年,千奇万怪只依然。
试从精舍先生问,定在包牺八卦前。
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
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
行尽桑麻九曲天,更寻佳处可留连。
如今归棹如掤箭,不似来时上水船。
扁舟费尽篙师力,咫尺平澜上不来。
山上风吹笙鹤声,山前人望翠云屏。
蓬莱枉觅瑶池路,不道人间有幔亭。
玉女峰前一棹歌,烟鬟雾髻动清波。
游人去后枫林夜,月满空山可奈何。
见说仙人此避秦,爱随流水一溪云。
花开花落无寻处,仿佛吹箫月夜闻。
千丈搀天翠壁高,定谁狡狯插遗樵。
神仙万里乘风去,更度槎丫个样桥。
山头有路接无尘,欲觅王孙试问津。
瞥向苍崖高处见,三三两两看游人。
巨石亭亭缺啮多,悬知千古也消磨。
人间正觅擎天柱,无奈风吹雨打何。
自有山来几许年,千奇万怪只依然。
试从精舍先生问,定在包牺八卦前。
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
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
行尽桑麻九曲天,更寻佳处可留连。
如今归棹如掤箭,不似来时上水船。
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泪与秋河相似,点点注天东。十载楼中新妇,九载天涯夫婿,首已似飞蓬。年光愁病里,心绪别离中。
咏春蚕,疑夏雁,泣秋蛩。几见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闻道十分消瘦,为我两番磨折,辛苦念梁鸿。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
咏春蚕,疑夏雁,泣秋蛩。几见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闻道十分消瘦,为我两番磨折,辛苦念梁鸿。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
世路如秋,万里萧条,君何所之。想鲈乡烟水,尚堪垂钓,虎丘泉石,尽可题诗。橙弄霜黄,芦飘雪白,何处西风无酒旗。经行地,有会心之事,好吐胸奇。
一邱封了要离。问世上男儿今有谁。但一尊相属,居然感慨,扁舟独往,可是嶔崎。齐邸歌鱼,扬州跨鹤,风味浅深君自知。匆匆去,算梅边春动,又是归期。
一邱封了要离。问世上男儿今有谁。但一尊相属,居然感慨,扁舟独往,可是嶔崎。齐邸歌鱼,扬州跨鹤,风味浅深君自知。匆匆去,算梅边春动,又是归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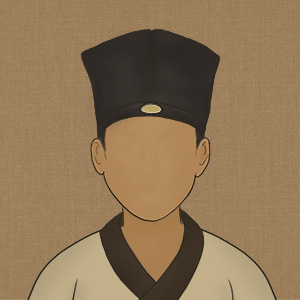 施绍莘
施绍莘 辛弃疾
辛弃疾 左丘明
左丘明 陈亮
陈亮 蒋士铨
蒋士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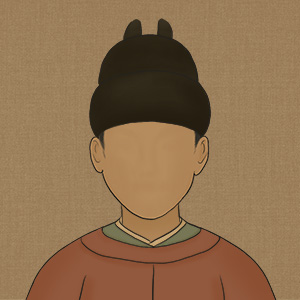 毛熙震
毛熙震 毛泽东
毛泽东 陈人杰
陈人杰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刘禹锡
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