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纪事一百韵
积水通旸谷,横流划大荒。山从波底拔,人向岛间忙。
喷薄鱼龙气,昭回日月光。溯源盘古埒,戡乱舜天强。
遗种滋蕃育,余黎浸炽昌。《隋书》名始著,《明史》氏衫彰。
久矣怀中夏,幡然耻夜郎。艰危勤栉沐,宛转达梯航。
鼢冒才开楚,椒聊已咏唐。翼缘侵沃灭,虢亦侍虞亡。
自此连三省,因而擅一方。辨戈承系统,当璧验真王。
世业经兴替,私衷倍悚惶。首先依定鼎,踵接贺垂裳。
序次句骊右,班联御幄傍。衮旒施祖考,币帛逮嫔嫱。
奉朔遵时宪,于东奠土疆。戚休萦眷注,灾患许扶匡。
习俗沿蒙昧,专员代测量。地稽吴越近,星订女牛祥。
属籍刊盟府,功宗纪太常。五朝修职贡,七姓效劻勷。
厥篚陈蕉苎,充闲罢骕骦。蛮笺翻侧理,阴火斸硫磺。
扇冀皇风拂,刀呈武库藏。鉴诚恒奖纳,厚往必优偿。
睿藻颁题额,彤云拥画梁。战图麟阁贮,辍赐雀屏张。
彝器樽兼卣,奇珍琥与璜。缤纷周黼黻,斑驳汉琳琅。
既普菁莪化,还贻翰墨香。凡兹宏在宥,孰是感能忘。
乃者遭多难,嗟哉悼幼殇。告哀循故典,嗣服进邮章。
举国知重耳,群情爱子臧。痛维藟庇本,敢谓雁分行。
摄位仔肩荷,殚精庶政康。慎封虔镇抚,主鬯妥烝尝。
惟帝恢无外,宣纶出未央。八驺迎簜节,双舸下虬洋。
存殁均焘怙,君臣俨对扬。祭怜新鬼小,恩溥旧邦长。
载启延宾馆,咸升敷命堂。瓦𤮊攒玳瑁,门牡閟鸳鸯。
围棘姑罗干,崇墉砺石墙。赳桓屯虎旅,瓯脱坼蜂房。
笳吹晨昏剧,饩牵旦夕将。挽输划独木,供亿顶柔筐。
亟见台米馈,翻愁跑用伤。醰醰澄酒醴,霍霍伺猪羊。
束缚蛇皮黑,支撑蟹距黄。鮔烘乾噬腊,米咂腻含浆。
漫说频加饭,何曾暂彻姜。平生几食料,异域具膏粱。
好证游仙梦,遐思选佛场。敲棋疑鹄至,仿帖眩鸾翔。
文惮韩苏健,诗惊李杜芒。沁脾咀蔗尾,燥吻擘瓜瓤。
不暑晴添热,非秋雨送凉。蛟涎朝更毒,蜃雾晚尤沧。
蜥蜴声如鹊,蚊蚊阵若蝗。但逢寒燠换,便觉起居妨。
吟啸消岑寂,登临展眺望。携童寻胜迹,杖策步层冈。
迤逦停舟港,参差系马枊。两崖排铁板,百雉巩金汤。
融结成都会,衣冠萃济跄。归仁藩分壮,守礼燕诒庆。
井养疏泉窦,师贞戢剑铓。申宫严禁卫,徼道设亭障。
弼教爰增律,誉髦并建痒。富须广树艺,暇即浚池隍。
欲继前规扩,全凭治法良。顺途招父老,憩坐话农桑。
质朴形殊琐,兜离语却详。公田卿以下,偕乐岁之穰。
薯蓣贫家糗,凫茨野处粮。钱轻鸠目刮,笔硬鹿毛僵。
剔抉螺称贝,陶镕锡号钢。民庞羞狗盗,里美贱狐倡。
志录犹仍误,咨诹待细商。迢遥南暨北,荏苒露为霜。
聆乐偏惆怅,闻鸡每激昂。扫除徐孺榻,点检郁林装。
赠贿仪终亵,坚辞意岂傏。裒编庋荩箧,丛绘袭巾箱。
客静搜残帙,奴顽笑涩囊。骈仓深比阱,麻力矮于床。
吉果圆揉粉,彩糕滑糁糖。菜肥搴苜蓿,面洁磨桃榔。
信宿奚求备,绸缪且预防。喧呼伐钲鼓,踊跃挂帆樯。
隐念祈呵护,斋心默祷禳。再看涛滚滚,又涉浸茫茫。
熟路沧溟阔,恬瀛圣泽瀼。回头夷壤杳,屈指岭梅芳。
曼寿皆欢喜,千官正拜飏。微忱徒绻缒,儤直后趋蹡。
缥缈瞻壶峤,晶荧认角亢。乘槎旋海屋,愿晋万年觞。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 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仙吕】【点绛唇】织履编席,能勾做大蜀皇帝,非容易。官里旦暮朝夕,闷似三江水。
【混江龙】唤了声关、张二弟,无言低首泪双垂;一会家眼前活现,一会家口内掂提。急煎煎御手频捶飞凤椅,扑籁籁痛泪常淹衮龙衣。每日家独上龙楼上,望荆州感叹,阆州伤悲。
【油葫芦】每日家作念煞关云长、张翼德,委得俺宣限急。西川途路受驱驰,每日知他过几重深山谷,不曾行十里平田地。恨征马宛四只蹄,不这般插翅般疾;踊虎躯纵彻黄金辔,果然道"心急马行迟"。
【天下乐】紧跐定葵花镫踅鞭催,走似飞坠的双镝,此腿脡无气力。换马处侧一会儿身,行行里吃一口儿食,无明夜不住地。
【醉扶归】若到荆州内,半米儿不宜迟,发送的关云长向北归。然后向阆州路上转驰驿,把关、张分付在君王手里,教他龙虎风云会。
【金盏儿】关将军但相持,无一个敢欺敌。素衣匹马单刀会,觑敌军如儿戏,不若土和泥。杀曹仁十万军,刺颜良万丈威。今日被坏人将你算,畅则为你大胆上落便宜。
【醉中天】义赦了严颜罪,鞭打的督邮死,当阳桥喝回个曹孟德。倒大个张车骑。今日被人死羊儿般剁了首级,全不见石亭驿!
【金盏儿】鞍马上不曾离,谁敢松动满身衣?恰离朝两个月零十日,劳而无役枉驱驰!一个鞭挑魂魄去,一个人和的哭声回。宣的个孝堂里关美髯,纸幡上汉张飞。
【赚煞】杀的那东吴家死尸骸堰住江心水,下溜头淋流着血汁。我教的茸茸蓑衣浑染的赤,变做了通红狮子毛衣。杀的他敢血淋漓,交吴越托推,一霎儿番为做太湖鬼。青鸦鸦岸儿,黄壤壤田地,马蹄儿踏做捣椒泥。
第二折
【南吕】【一枝花】早晨间占《易》理,夜后观乾象。据贼星增焰彩,将星短光芒。朝野内度量。正俺南边上,白虹贯日光。低首参详,怎有这场景象?
【梁州】单注着东吴国一员骁将,砍折俺西蜀家两条金梁。这一场苦痛谁承望?再靠谁挟人捉将?再靠谁展土开疆?做宰相几曾做卿相,做君王那个做君王?布衣间昆仲心肠。再不看官渡口剑刺颜良,古城下刀诛蔡阳,石亭驿手挎袁襄!殿下帝王,行思坐想,正南下望,知祸起自天降。宣到我朝下若问当,着甚话声扬?
【隔尾】这南阳耕臾村诸亮,辅佐着洪福齐天汉帝主,一自为臣不曾把君诳。这场勾当,不由我索向君王行酝酿个谎。
【牧羊关】张达那贼禽兽,有甚早难近傍?不走了糜竺、糜芳!咱西蜀家威风,俺敢将东吴家灭相。我直教金鼓震、倾人胆,土雨溅的日无光;马蹄儿踏碎金陵府,鞭梢儿蘸干扬子江。
【贺新郎】官里行行坐坐则是关、张,常则是挑在舌尖,不离了心上。每日家作念的如心痒,没日不心劳意攘,常则是心绪悲伤。白昼间频作念,到晚后越思量,方信道"梦是心头想";但合眼早逢着翼德,才做梦可早见云长。
【牧羊关】板筑的商傅说,钓鱼儿姜吕望,这两个梦善感动历代君王。这梦先应先知,臣则是误打误撞。蝴蝶迷庄子,宋玉赴高唐,世事云千变,浮生梦一场。
【收尾】不能勾侵天松柏长千丈,则落的盖世功名纸半张!关将军美形状,张将军猛势况,再何时得相访?英雄归九泉壤,则落的河边堤土坡上、钉下个缆桩。坐着条担杖,则落的村酒渔樵话儿讲。
第三折
【中吕】【粉蝶儿】运去时过,谁承望有这场丧身灾祸?忆当年铁马金戈,自桃园初结义,把尊兄辅佐。共敌军擂鼓鸣锣,谁不怕俺弟兄三个!
【醉春风】安喜县把督邮鞭,当阳桥将曹操喝,共吕温侯配战九十合,那其间也是我、我!壮志消磨,暮年折挫,今日向匹夫行伏落。
【红绣鞋】九尺躯阴云里偌大,三缕髯把玉带垂过,正是俺荆州里的二哥哥。咱是阴鬼,怎敢陷他,唬的我向阴云中无处躲。
【迎仙客】居在人间世,则合把路上经过。向阴云中步行因甚么?在常爪关西把他围绕合,今日小校无多,一部从十余个。
【石榴花】往常开怀常是笑呵呵,绛云也似丹脸若频婆;今日卧蚕眉瞅定面没罗,却是为何?雨泪如梭,割舍了向前先搀过,见咱呵恐怕收罗。行行里恐惧明闻破,省可里倒把虎躯挪。
【斗鹌鹑】哥哥道你是阴魂,兄弟是甚么?用舍行藏,尽言始末:则为帐下张达那厮厮嗔喝,兄弟更性似火;我本意待侑他,谁想他兴心坏我!
【上小楼】则为咱当年勇过,将人折挫,石亭驿上袁襄怎生结未?恼犯我,拿住他,天灵摔破,亏图了他怎生饶过!
【幺篇】哥哥你自暗约,这事非小可。投至的曹操、孙权,鼎足三分,社稷山河。筋厮锁,俺三个,同行同坐,怎先亡了咱弟兄两个?
【哨遍】提起来把荆州摔破,争奈小兄弟也向壕中卧!云雾里自评薄,刘封那厮于礼如何?把那厮碎剐割!糜芳、糜竺、帐下张达,显见的东吴躲。先惊觉与军师诸葛,后入宫庭,托梦与哥哥。军临汉上马嘶风,尸堰满江心血流波;休想逃亡,没处潜藏,怎生的躲?
【耍孩儿】西蜀家气势威风大,助鬼兵全无坎坷;糜芳、糜竺共张达,待奔波怎地奔波?直取了汉上才还国,不杀了贼臣不讲和!若是都拿了,好生的将护,省可里拖磨。
【三煞】君王索怀痛忧,报了仇也快活。除了刘封,槛车里囚着三个。并无喜况敲金镫,有甚心情和凯歌?若是将贼臣破,君王将咱祭奠,也不用道场锣钹。
【二煞】烧残半堆柴,支起九顶镬,把那厮四肢梢一节节钢刀剉,亏图了肠肚鸡鸦啄,数算了肥膏猛虎拖。咱可灵位上端然坐,也不用僧人持咒,道士宣科。
【收尾】也不用香共灯、酒共果,但得那腔子里的热血往空泼,超度了哥哥发奠我。
第四折
【正宫】【端正好】任劬劳,空生爱,死魂儿有国难投!横亡在三个贼臣手,无一个亲人救。
【滚绣球】俺哥哥丹凤之目,兄弟虎豹头,中他人机彀,死的来不如个虾蟹泥鳅!我也曾鞭督邮,俺哥哥诛文丑,暗灭了车胄,虎牢关酣战温侯。咱人"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壮志难酬!
【倘秀才】往常真户尉见咱当胸叉手,今日见纸判官趋前退后,元来这做鬼的比阳人不自由!立在丹墀内,不由我泪交流,不见一班儿故友。
【滚绣球】那其间正暮秋,九月九,正是帝王的天寿。列丹墀宰相王侯,攘的我奉玉瓯进御酒,一齐山寿,官里回言道臣宰千秋。往常摆满宫彩女在阶基下,今日驾一片愁云在殿角头,痛泪交流。
【叨叨令】碧粼粼绿水波纹皱,疏刺刺玉殿香风透。皂朝靴跐不响玻璃甃,白象笏打不响黄金兽。元来咱死了也么哥,咱死了也么哥!耳听银箭和更漏。
【倘秀才】官里向龙床上高声问候,臣向灯影内恓惶顿首。躲避着君王,倒退着走;只管里问缘由,欢容儿抖擞。
【呆骨朵】终是三十年交契怀着熟,咱心相爱志意相投。绕着二兄长根前,不离了小兄弟左右。一个是急飐飐云间凤,一个是威凛凛山中兽。昏惨惨风内灯,虚飘飘水上沤。
【倘秀才】官里身躯在龙楼凤楼,魂魄赴荆州、阆州,争知两座砖城换做土丘!天曹不受,地府难收,无一个去就!
【滚绣球】官里恨不休,怨不休,更怕俺不知你那勤厚,为甚俺死魂儿全不相瞅?叙故旧,厮问候,想那说来的前咒书,桃园中宰白马乌牛。结交兄长存终始,俺伏侍君王不到头,心绪悠悠。
【三煞】来日教诸葛将二愚男将引,丁宁奏,两行泪才那不断头。官里紧紧的相留,怕不待慢慢的等候,怎禁那滴滴铜壶,点点更筹。久停久住,频去频来,添闷添愁!来时节玉蟾出东海,去节残月下西楼。
【二煞】相逐着古道狂风走,赶定长江雪浪流。痛哭悲凉,少添僝僽,拜辞了龙颜,苦度春秋。今番若不说,后过难来,千则千休;丁宁说透,分明的报冤仇。
【煞尾】饱谙世事慵开口,会尽人间只点头。火速的驱军校戈矛,驻马向长江雪浪流。活拿住糜芳共糜竺,阆州里张达槛车内囚。杵尖上挑定四颗头,腔子内血向成都闹市里流,强如与俺一千小盏黄封头祭酒!
山翁醉,仙子扶,草新词粉笺霜兔。船头晚凉湖上雨,锦鸳鸯傍花飞去。
春晚二首
弹珠泪,上宝车,柳青青渭城官舍。杜鹃又啼春去也,两无情水流花谢。
秾妆褪,苏幕遮,过清明小楼春夜。剔银灯快将诗句写,晓风寒海棠花谢。
春情
空凝伫,不见他,画帘垂柳花飞过。髻云偏翠斜金凤亸,碧痕香绣窗茸唾。
水爆仗
椷云气,走电光,翠烟流洞庭湖上。起蛰龙一声何处响?碎桃花禹门春浪。
春晚
寻花径,梦草池,乳莺啼牡丹开未?荒凉故园春事已,谢东风补红添翠。
玄文馆雪夜饮金盘露食马头
寻梅处,泛剡图,白模糊小桥无路。仙霞洞中清事足,金盘露马头香玉。
席上为真士陈玉林作
溪船去,山竹折,玉成林小窗清夜。销金党家何处也?搅琼酥惠船明月。
春思
娇莺韵,乳燕声,盼归舟玉人成病。趁东风远游不见影,浪儿每柳花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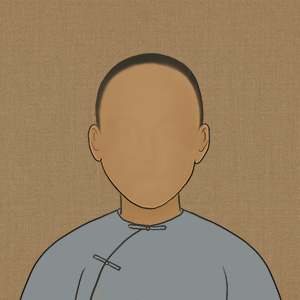 费锡章
费锡章 左丘明
左丘明 关汉卿
关汉卿 张可久
张可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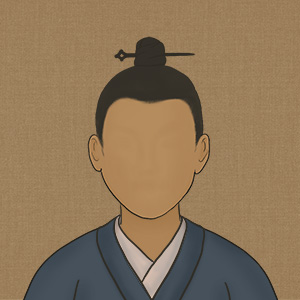 徐再思
徐再思 陈克
陈克 冯延巳
冯延巳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李煜
李煜 苏轼
苏轼 王谌
王谌